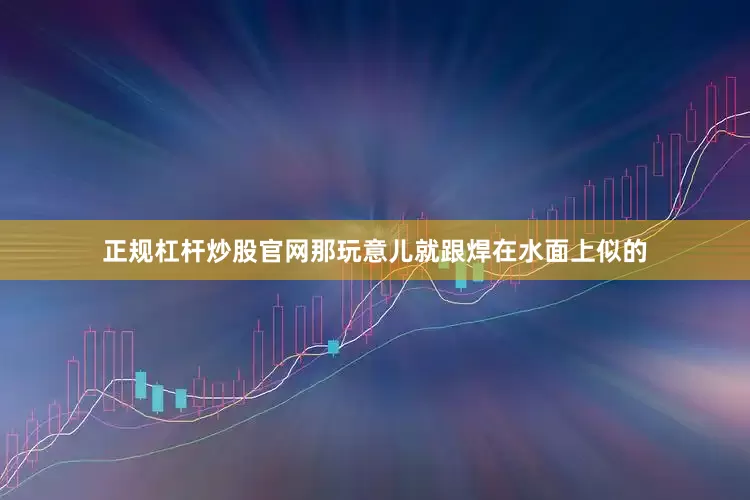1979年1月的一个下午,北京京西宾馆的会议室里坐着160多位理论界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刚讲完开场白,底下就开始窃窃私语。谁也没想到,几天后会有24个人集体"造反",要求撤掉《红旗》杂志的整个编辑部。
这事说起来真够讽刺的。《红旗》杂志当年可是威风八面,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称"两报一刊",地位那叫一个崇高。可就是这么个权威刊物,居然被自己人给集体炮轰了。
当年的辉煌岁月
回到1958年,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办个理论刊物,这个想法其实早就在他心里盘算了好几年。1955年的时候他就说过,各省市都得办好刊物。

你说巧不巧,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第一天,毛主席就列了25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第24个就是"出版理论刊物"。看得出来,这事在他心里分量不轻。
《红旗》这个名字一听就让人热血沸腾。更厉害的是,毛主席亲自为这本杂志题写了20多个刊头,还在旁边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一个大国领袖为了杂志刊头的艺术效果反复琢磨,你说这得多用心。
编委会的阵容更是豪华得不行。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陆定一、胡乔木……这些名字随便拿出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毛主席一个一个亲自挑选,足见对这本杂志的重视。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创刊。纯白色封面上印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红色"红旗"二字,就像红绸在飘舞。毛主席不光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后来还经常向杂志推荐文章,有时候自己动手修改稿件。
有一次,毛主席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写的机床设计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就以《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给作者写信约稿。堂堂一国领袖给大学老师写约稿信,这在今天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年代的《红旗》杂志确实厉害。每期发行后,党员干部争相传阅,理论界把它当风向标。杂志社内部还搞了些有趣的传统,比如有个叫"许辛学"的笔名,其实是"虚心学"的谐音。

在思想解放中迷失方向
时间到了1978年,这一年对中国意义重大。刚刚走出历史阴霾的中国正在寻找前进方向,可《红旗》杂志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沉默。
说起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那真是场了不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很多人的思想给箍住了。按这个逻辑,很多历史问题都没法解决,改革开放更是无从谈起。
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新华社当天转发全国。这文章就像春雷一样,瞬间打破了思想沉寂。
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这篇重要文章,可《红旗》杂志却保持了令人困惑的沉默。这种沉默在当时特别扎眼,因为《红旗》的态度往往被当作党中央的风向标。

恰好这时候,熊复走马上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他上任时杂志社正在恢复元气,工作刚开始正常运转。巧的是,他接手的时间正好是真理标准讨论最热烈的时候。
熊复对《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态度很明确——不赞成。他认为有些报纸用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讲话,但"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讲话,还很难说"。他还说,现在应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强调发展创新。最让人吃惊的是,他还质问:"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理论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在这种想法指导下,《红旗》杂志做出了"不介入"的决定。熊复明确表示:《红旗》杂志不参加这场讨论,还说《红旗》要"一花独放"。
这种态度让人摸不着头脑。一向承担理论指导责任的《红旗》,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理论讨论中选择退出?
更让人无语的是,6、7月份的理论讨论会,《红旗》杂志要么不派人参加,要么派了人也不发言,借口是"我们正在搞运动,对这个问题没研究"。8月份杂志社准备发表《重温〈实践论〉》的文章,熊复都不让发表。

随着时间推移,《红旗》杂志的处境越来越尴尬。社会上开始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说法。这种对比太鲜明了——《人民日报》因为积极参与讨论受欢迎,《红旗》杂志因为保持沉默被边缘化。
有人向熊复反映《红旗》不表态受到责难,他竟然回答:"不要怕孤立,怕什么?"甚至还说"你们感到被动,我才不被动呢!"这种固执让人无奈。
其实从今天看,熊复当时的处境确实不容易。他刚上任,面对这么重大的理论问题,压力肯定很大。他后来也承认,自己长期脱离实际,对形势变化没有敏感性。
可是,历史不会因为个人困难而停步。当全国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时,《红旗》杂志的沉默显得特别突兀。这种沉默不只损害了杂志声誉,更重要的是背离了理论刊物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务虚会上的激烈交锋
1979年1月18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京西宾馆开幕。这次会议来了160多人,包括理论界各路人马,还有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胡耀邦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给整个会议定了调。他说这次会议要总结经验、分清是非,研究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对于经历了多年思想禁锢的理论工作者来说,这种自由讨论的氛围简直像久旱逢甘露。
会议进行到一定阶段,问题开始浮现。当讨论深入到具体理论实践问题时,不同观点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如何看待《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表现上,争论异常激烈。
就在这时候,一份让所有人震惊的联名信出现了。24名同志联名上书,要求彻底改组《红旗》杂志编辑部。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问题严重性——不是一两个人的个人意见,而是相当一部分与会者的集体声音。
这24个人在党内都有影响力,有些还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们在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红旗》杂志的问题,认为编辑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表现完全背离了理论刊物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消息很快在会场传开,引起轩然大波。支持改革的同志拍手叫好,认为这是打破僵局的关键一步。另一些同志则感到震惊,没想到批评声音这么强烈、这么集中。

《红旗》杂志编辑部负责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试图为自己辩护,说被批评的文章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成员写的,与《红旗》编辑部没关系。
可这种辩解显然平息不了大家的不满。与会者关注的不是某篇具体文章,而是《红旗》杂志在整个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根本态度。那种长期沉默,那种明显的"不介入"姿态,已经深深伤害了党内外对权威理论刊物的信任。
面对强烈批评,胡耀邦表现出成熟政治家的风度。他亲自约见熊复谈话,语重心长地说:"这只是部分同志没跟上形势,有错误没关系,也没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知错能改即可。"
这话听起来平和,实际上暗含深刻政治智慧。既给了当事人台阶下,又明确表达了中央的基本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党内民主讨论精神——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批评错误,关键是要有改正错误的诚意和行动。
调查真相与深刻反思
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超出所有人想象。胡耀邦派出专门调查组,要彻底搞清楚问题症结。这不是简单敷衍,而是要通过深入调查分析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调查工作进行得很细致,涉及面也很广。调查组不只查明具体事实,更要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关注此事的同志都感到欣慰——党中央确实要解决问题,不是遮掩问题。
1979年5月29日,调查结果出来了。报告指出文章内容和观点有错误,但根据作者情况、写作经过、写作背景等方面看,这篇文章并不影射什么,也不是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不能说是政治阴谋。
面对调查结果,胡耀邦展现了特有的风度和智慧。他在报告上写了四句话:"务虚会上闷雷几声,《红旗》社内一场虚惊,毛著编委排难解纷,文坛老将息事宁人。"这四句话既总结了事件经过,又体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展现了政治家的胸怀格局。
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感到温暖。没有过度政治化,没有无原则上纲上线,而是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妥善化解矛盾。
虽然具体文章问题得到澄清,但《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整体表现仍让很多同志不满。考虑到务虚会上多名同志对熊复心存不满,杂志社内也有工作人员联合上书,中央做了罢免熊复总编辑职位的决定。

这个决定算是情理之中。作为重要理论刊物总编辑,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论自觉性,确实难以继续担当重任。
熊复本人对结果也有深刻反思。进入新世纪后,已经卸任多年的熊复谈起1978年仍然唏嘘不已。他勇于承担错误,深刻剖析了其中原因:受过时教育熏陶影响、长期脱离实际和社会脱节、本位思想严重对形势变化没敏感性。
这种坦诚自我批评体现了老党员的觉悟和品格。其实熊复的问题在当时不是孤立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很多人都面临思想观念转变问题。
历史转折与新的开始
在深刻反思基础上,党中央对理论宣传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对《红旗》杂志给予具体指导。他不只同意把自己的文章、讲话以《红旗》编辑部、评论员名义发表,还对送审稿件严格把关。

这种做法体现了中央对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不是简单批评否定,而是积极指导帮助。1979年12月发生一件事,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没通知《红旗》杂志参加。《红旗》编辑部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写信给胡耀邦反映,胡耀邦立即回信承认错误并表示理解。
这封回信充满人情味,体现了领导者胸怀。胡耀邦在信中说:"《红旗》发生的失误,我认为早已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误的历史。我们只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这种态度让《红旗》杂志同志深受感动,也为杂志重新振作创造了良好环境。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对理论指导需求越来越迫切。《红旗》杂志努力适应新形势,在理论宣传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工作。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对理论刊物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这个历史性时刻标志着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进入新阶段。
《求是》杂志的创刊,主办单位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校"。这种变化不只是形式上的,更体现了对理论工作新的定位和要求。
《红旗》杂志停刊不意味着历史作用的否定。它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道,曾为传递党中央权威声音,为指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不可磨灭贡献。

《求是》杂志创刊是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坚持党刊姓党、政治家办刊原则。《求是》这个名字本身就体现实事求是精神,体现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回顾1979年那场关于《红旗》杂志的争论,这不只是对一个杂志的批评,更是对一种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的反思纠正。24名同志的联名建议体现了党内民主讨论优良传统,是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品格。
从《红旗》到《求是》,这不只是两个杂志的历史传承,更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品格的生动体现——既坚持真理又修正错误,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既实事求是又开拓创新。
金领速配-专业配资炒股网-股票配资平台点评-股票配资怎么玩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